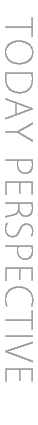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永远的镜像
——“善与恶”在中国文学中的表达与缺失
夏维东
关于文学,可能没有比别林斯基说得更简洁更深刻的了,这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评论大家说:“文学是人学”;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文学就是对人性的表达。“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好,“性本恶”(荀子)也罢,善与恶注定了是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永远的镜像。
自汉代志异、六朝志怪、唐传奇直到宋的话本小说,中国传统小说才定下型来,章回小说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中叶。历朝历代的章回小说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道德观,直接表明了社会对善恶的态度。这种道德观的基础是儒家的伦常和佛家的因果报应。在古典小说中大名鼎鼎的《金瓶梅》就非常有代表性。
《金瓶梅》的主要版本有两个:词话本和绣像本(崇祯本)。这两个版本的文词差别极大,前者直白,后者文雅,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版本在主题上的差异。田晓菲在《世间两部金瓶梅》一文里说得非常到位:“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而绣像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西门庆当然是两个版本的反面教材了,词话本开的处方是人当走中庸之路,持盈慎满,不可纵欲;绣像本则干脆来个六根清净,远离红尘,了却俗念。
《金瓶梅》两个版本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小说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在这方面也同样“古典”。拿“伤痕小说”来说,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泾渭分明。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善恶标准不再是以传统道德为准绳,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了,即跟着“四人帮”极左路线走的是坏人,反之则是好人。作家严歌苓在谈到“伤痕小说”时说:“我看到伤痕文学的时候,想,这样的小说也叫小说?”(《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我们》月刊2003年第六期)伤痕小说的失败在于其缺乏对人性共性的表达,对“文革”没有认识的外国人也许对那一幕幕不乏真实的悲剧缺乏共鸣。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事过境迁,当我们从最初的悲愤中冷静下来,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四人帮”没有被打倒,那么善恶是不是就易位了?这种相对的善恶观无法抵达本质上的深刻。
“文革”是苦难,日本侵华是苦难,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乱是苦难,中华民族所受的苦楚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少。不是说“苦难是精神财富”吗?可为什么这个“精神”财富没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贫血。
我们拿不出一部与《忏悔录》、《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复活》、《巴黎圣母院》等量齐观的伟大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技巧有多好,人物形像有多丰满,故事情节多么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人物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挣扎,在这样的挣扎中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博大与深刻。如果把技巧、人物形像和情节当作形而下的话,那么对于精神世界的剖析与揭示就是形而上。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伟大的杰作正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和谐。
卢梭在《忏悔录》开头就说:“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四页)这段话与《约翰福音》中的一段叙述遥相呼应,耶稣对那些准备用石头砸死“坏女人”的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耶稣指出了人类本质上的罪性,没有人能够反驳,于是那些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就是那个把自己拎出来放到众人面前的“坏女人”,他是在向上帝忏悔,而不是祈求世人原谅。他不需要别人谅解,他把自己竖立为一面镜子,那些对他指指点点的人都将在心灵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卑微的形像。
卢梭把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览无遗地袒露出来,在习惯“为尊者讳”的中国人看来,他简直是在自毁长城。要知道,写《忏悔录》之前的卢梭已经是法兰西文化界的大人物,是当时最著名的“平民思想家”。他不愿像蒙田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只有可爱小缺点的伟人,但他的真诚却让他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学意义上的伟人。传记能成为文学名著的极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其一,卢梭的《忏悔录》毫无疑问也是其一。它以一种淳朴、清新的叙事风格和人格的力量推动了法兰西十九世纪的文学革命。
忏悔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识,具有位格的上帝是忏悔的倾听者,在倾诉中,伟大的作品诞生了。在这些作品中,人性中的共性的东西——罪得到表达,并且指出了罪在终极意义上的救赎。罪与救赎是两位一体的。救赎者与定罪者也是两位一体的,没有定罪的权柄就意味着没有赦免的权力。如果对罪在终极意义上缺乏认识,那么单纯对罪的表现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参照物的标准是可疑的——要么是以政治或国家意识形态为依据,比如说中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传统道德为标准,而那些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变化,宋、明文学中的烈女在现在看来大概是愚昧的;那些“替天行道”的大侠们真的是正义与善良的化身吗?那些大侠们放在现在的社会可能被判一百个死刑都不嫌多,少说也是个无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大书讲的其实就是信仰。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的内心秘密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中表露无遗,而他们的生活态度直接取决于他们对待上帝与灵魂的看法。别以为这部中译本长达八十万言的小说是说教而枯燥无味,围绕着杀父的疑案,整个案件从发生到水落石出不过一周时间,可以想象情节推动得有多快!与一般谋杀题材的商业小说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不是谁是凶手,而是凶手为什么成为凶手。在对案情的层层剥离中,包裹在人物肉体里面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小说因此抵达了通俗侦探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精神高度:信仰和无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物在相同的时空里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形成多声部的合唱,后世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复调小说”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已经运用自如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陀氏是“复调小说”的鼻祖,但他肯定是先驱者之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明显受到《卡》叙事模式的影响。
老卡拉马佐夫是恶的化身,人性卑劣面的“集大成者”:贪婪、自私、冷酷、亵渎等等。他不择手段攒了万贯家财,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斯梅尔佳可夫杀了。这个弑父的儿子是一个疯女人被老卡拉马佐夫强奸后生下的,他是他老子的翻版,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卡拉马佐夫被他杀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斯梅尔佳可夫杀了父亲后,嫁祸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是个矛盾体,既高尚又卑鄙,心灵挣扎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是个聂赫留朵夫式的人物。他在审判前的夜晚,在人类苦难与基督受难的思考中,他的精神“复活”了。尽管他没有杀人,可他愿意背负起十字架,借以纯净自己曾经浑浊的灵魂。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