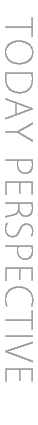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想象力挑战生活智慧
陈冲
这又是个简化过的标题。全写出来,应该是“作家的想象力挑战批评家的生活智慧”。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已经揭晓。《北京文学》在它的选刊“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上,集中重发了所有获奖的中、短篇小说,还请人分别对中篇和短篇做了综合性的点评。这是件好事儿。只是其中的中篇点评,偏偏请出了通常被认为爱挑毛病的李建军先生,来干这评功摆好的活儿,就有了点鬼使神差的味道。于是,在李先生讲到获奖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时,我们就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应为冰柜)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究竟是怎样的描写呢?是这样的:
“我觉得秘密一定藏在冰柜里。我……掀起冰柜盖。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
矿工蒋百的“失踪”之谜,是这部中篇小说贯穿全篇的悬念。谜底揭开,原来“失踪”的蒋百实际上死于一场全班十人无一生还的矿难,而按规定,恰恰是死亡十人以上的矿难必须上报,所以矿方以重金换取蒋百嫂同意用这种方式将丈夫视为“失踪”,“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
单论“描写”,确实很有震撼力。
不过,我读这段描写时,想到的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是我习惯的译法),也不是萧红或陈忠实,而是一个很缺德的疑问:这事儿可能吗?蒋百遇到的矿难具体是哪种事故,作品没有明说,虽然从“面容被严重损毁”看,可能是瓦斯爆炸。但不管是瓦斯爆炸,还是冒顶或透水,以我的了解,所有重大煤矿矿难的抢救工作都是有难度、有危险的,从了解情况,到制订方案,到组织人力设备,到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才能展开施救。因而,遇难矿工的遗体,绝无可能在矿难发生后两三个小时内就升井送上地面,并即刻装进事先备好的冰柜。人的尸体一旦僵硬,就再也无法将其弯曲,使之“蜷腿”、“坐”、“双臂交织”。最近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那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将其遗体装入冰柜。虽然从行凶到藏尸是连续进行的,而且从凶杀现场到放冰柜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同一城市,装入冰柜的尸体已经被肢解过了。
我很赞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立意。单是那博爱精神,就弥足珍贵。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博爱”原是和“平等、“自由”三位一体的,可是我们在200多年后重新热衷于念叨启蒙时,已经忘记了博爱。作为读者,读到这样的硬伤时,真是为作家惋惜。那么作为批评家,应该怎样看待它呢?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就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一位批评家单把这处硬伤挑出来大加赞美,说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总归说不过去吧。
王松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红莓花儿开》,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4期,同年第10期《小说选刊》头题转载,并同期刊出了作家的创作谈。这篇小说的立意也很好,写法更有独到之处,使作品的内涵具有普泛的能指。这个中篇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能否用电池来引爆炸药。小学二年级学生华二傻,为了向同学们证明1.5伏直流电的威力(从而证明电池能够引爆炸药),搞来了整流器和变压器,却受到罗老师的嘲笑。罗老师问明该变压器(实际应为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1.5 伏后,不顾华二傻“它的电流比电池要大得多”的警告,让华二傻接通电源,然后把(接通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线放进嘴里。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华二傻的错误,结果却是“那两根电线在罗老师的舌头上发出‘叭’的一声爆响,接着罗老师突然张大嘴,鼓起眼,做出一副非常夸张的表情,跟着整个人就仰身朝后咕咚一声摔在讲台上。这时那两根电线仍还牢牢地通向罗老师的嘴里,所以,他倒在地上两腿还在不停地抽搐,看上去就像在发癫痫。”单就描写而论,称得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但是,我那个缺德的疑问又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据我所知,会不会让人有“触电”的感觉或后果,只与电压有关,与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完全无关。让人“触电”的电流是通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导线里的电流。由于人是不良导体,电阻(R)较高,当电压(U)不高时,能通过人体的电流(I)也就不多。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电工知识,用公式来描述,就是U=IR。
王松是学数学的,不知道U=IR,是个缺憾,但不好深责。军旅作家写战争也不能保证不出错。朱秀海的中篇小说《出征夜》,也是《小说选刊》(2003年第10期)的头题,同样也有作家的同期创作谈。诚如编者所赞誉的那样,“可贵在选取了一个鲜为人用的角度”,“没有直接描写战场”,而是写在打响之前,两个政工干部领着民工连为即将牺牲的人挖墓坑,而“将要牺牲的人数已经被十分‘理论’地预计了出来”,因而“生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对牺牲人数进行预计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笔,作家写来用了两千多字。作家如此着力渲染自有其道理,我只摘出其中最核心的“理论计算”:“对面的敌人是一个营”,“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明天我们要准备牺牲四个营,也就是一个加强团”,“现在我们一个团的编制是三千八百人”,“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必须挖出三千八百个墓坑”,因为“没有那么多民工连”,可以“先挖出其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千个”,然后“明天白天接着挖”。我得承认,这也真让我震撼过一会儿,不过后来那个缺德的疑问还是止不住地冒出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一个计算:以死3800人的代价去打掉敌人的一个营,这个仗打得吗?好吧,就算那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点,必须不计代价地拿下来。可是,如果阵亡的人数是3800,又会有多少人负伤(按同样道理,也得根据这个数字准备战地急救)呢?姑且按1:3计算,那么负伤和阵亡总共约15000人。就算这是一次极惨烈的战斗,伤亡总数占到参战人数的一半,那么投入的总兵力也不会少于30000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面对敌方一个营,居然能有效地展开我方三个师的兵力。想了想,明白了。在这个“理论计算”中,理论是对的,但计算却在一系列环节上不断出错,才得出这个3800的结果。一个个地指出这些环节太烦琐,就留给读者当益智题做着玩吧。
麦家要聪明一些。他在《暗算》中犯了一个错误。其中的“听风”,写四个人受审查的事,其中的革命者要在受审查的同时把情报送出去,而这个情报,即全篇的核心悬念,就是被捕者已经叛变。可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秘密工作都遵循一条基本原则:一旦有人被捕,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绝对不允许心存侥幸。也就是说,这个悬念其实是不成立的。此后,麦家又写了一部长篇《风声》,同样是四个人受审查,同样是其中之一还要送出一个重要情报,只是这个情报不同了,改成敌人已经破译了我方的密电,而我方还不知道。这就没问题了。麦家以新作改正了旧作中的错误,但他并不明说,却玩了个花活,说是“《暗算》面世以后,上海的一位大学教授”特意找到他,讲了其父早年一段类似的、但更精彩的故事,“由此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写了《风声》。聪明是真聪明,但有戏弄读者之嫌。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硬伤——不是哪一个局部弄错了,而是整个儿弄错了。对于出现这类硬伤,我的感觉也不仅是惋惜了。比如当“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时尚以后,一些作家纷纷挺身而出,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抱打不平,以至形成了某种类似母题的题旨: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甚至取得了某种“成功”,却仍然不被接受为城市的一员,使他们觉得所在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同,因而让我们的作家深感不公。这方面最显豁的例子,当推《明惠的圣诞》(邵丽)。在为数可观的同类作品中,此作并无多少特别之处,因其刚获鲁奖,故称“显豁”。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个对某种社会现象如何认知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个常识问题。农民进城务工,政府从态度上,政策上,特别是制度设计上,能否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各种公共资源提供的方便和实惠,确实存在着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但是他多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主要是个社会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那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常被表述为“一代人”的时间。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定理”,是由“社会”本身决定的,就像U=IR是由“自然”本身决定的一样。所以,对这个定理进行道德判断,就跟对U=IR进行道德判断一样地无效。
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有客观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作家相对好办些,用到哪样了,如果知识储备中没有,可以去查资料或请教,涉及的领域有限。批评家则困难多了,他得面对所有作家们涉及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当作家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查资料或请教,越来越喜欢单凭想象力去对付时,我都替批评家们发愁了。这已经不是知识储备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智慧问题。它需要对种种可疑的东西具有敏锐的直觉。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天真,凡不知道的,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真的就可以忽略不计?就不影响它发表,不影响它被多家选刊转载,不影响它获奖,包括鲁迅文学奖,不影响它为同一作家在四届中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已经和作家无关,关涉的仅仅是一个奖项的信誉。)我在上面多次提到作品发表、转载的刊物,是因为我把这也视为一种广义的批评。的确,有些硬伤只关乎次要的局部,对作品的整体价值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但我上面涉及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会不会在长此以往后的某一天,我们的作品中将充满着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而批评家们则对此赞不绝口?出错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对出错的态度。我知道不可能为此立一条规矩,何况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有规矩也可以不遵守的年月。但我仍然想,如果我们对文学、对创作、对批评真是严肃的、诚实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出错的作家,发表、转载它的刊物,为它叫过好的批评家,为它授过奖的奖项及其评委,都应该对读者有所交待,做个说明和更正。能道个歉就更好了。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