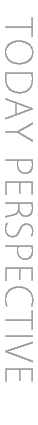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
黄孝阳
传统文学观,讲的是“写什么”与“怎么写”。其框架基本上是以牛顿等物理学家为代表所构建的经典物理大厦。我在《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小说笔记》等文论中作过一些陈述。它们并非我的发现。是写作者们谙熟的常识。我不过是用了一些比较好看的手法进行归纳、分析。
物理,格物致知,研究宇宙万物其内部结构、相互作用等。物,物质的结构、性质;理,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它从物出发,讲究观察与实证。它是此岸。文学是彼岸。是梦。承载祝祭。人们以梦为马,在时间的荒涯中想像宇宙的尽头。人从哪里来?是谁?在这里干什么?文学从心灵出发,帮助我们理解人、宇宙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在这些最基本、最永恒的问题上,文学与物理相通。这些也还是常识。物理学是发展着的。十七世纪以前,是经验物理的萌芽时期。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以经典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经典电磁场理论为支柱的经典物理的辉煌殿堂在大地上出现。这是一幢庄严雄伟的建筑物。人们相信“物理学已经终结,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集大成的体系来解决,而不会再有任何真正激动人心的发现了”。那时的人们,认为自己就要掌握上帝造物的奥秘。但到二十世纪初,相对论与量子理论横空出世。这场由“两朵乌云”带来的暴雨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文学亦不例外。它也是这样一棵不断生长着的树。我们来到树上,看见天空。
为什么要提量子文学?经典物理主要研究“低速宏观”的物理现象,若所研究的对象接近光速又或违背宏观,其理论基本都不成立。所谓“低速宏观”——也就是时间与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呈现出的为肉眼所感知的现象。传统小说大抵是在这个范畴中起转承合。“剃头匠李大碗儿来到龙凤镇的第三个年头,一个叫英儿的白脸寡妇在村庄后的大水渠边,生下他的第二个男孩。”时间、空间、人物、职业,甚至说可能要发生的故事,在这样一句话里,都得到了确认与暗示。这里的时空概念是人们共有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时间与空间是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小说对时间的处理非常复杂,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者用数十页书写他在床上辗转反复,读者用了一天时间才看完他的几分钟,这是时间的膨胀,是对空间的微观。显然,它就不适用于“低速宏观”下的那套传统文学的话语体系。否则结论一定荒谬。欧兰多夫出版社的主编给普鲁斯特写了一封退稿信,“乖乖,我从颈部以上的部分可能都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一个男子汉怎会需要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入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普鲁斯特本人对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手里登峰造极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屑,称他们的作品为“一张抄录了粗线条和外表的可怜的清单”。这种相互诋毁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看看那些已被公认为大师的作家们吧,其措辞之恶毒着实令后人汗颜,也大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文人相轻?为何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大师们也要怒眼相向,甚至不惜把死者从坟墓里扒出鞭挞?大师人品太差吗?这是一种解释。贵为大师,要比普通人享有更多特权,道德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公众也服膺这点。莎士比亚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莫泊桑是淫乱之徒,生于放荡,死于梅毒。乔伊斯到处借钱赖账。但这些不是根本原因,不乱搞的大师也是有的,可谈及文学观念时,他们也要跳出来决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岐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属于彼此打倒的敌我关系。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革你的命。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他们所描述的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拥有一个共同之名:时间与空间。
时间是一个箭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也是一个钟摆,以星期、月份为单位循环往复。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特质同时存在于时间内部,且往往为我们所忽视。时间是伟大的独裁者,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力,其指纹却乱七八糟,靠拢、分开、交错、碰撞、吞噬、旋转。要理解它,要费点劲。我在《蝴蝶》中写道:“我们无法同时处在不同的空间来观察时间,事实上空间亦有无数,平行或交错,如云蒸雾蔚,并朝生暮死。它是一纵,时间是一横,两者笔直交集,便是此刻。若它发生一点变形,又或时间略微有些扭曲,那此刻或许有你没我或许有我没你又或许我们皆不存在又或许我正是那窘迫的少年,你却是那位正试图靠近他搭讪的红发女人。”空间是三维的,加上时间这个要素,成为四维。关于空间的概念有许多哲学上与科学上的争议。在一般人的眼里,空间就是一个装东西的杯子。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康德把空间概念归结为人类理性的直观知觉,是一种先验存在的观念。物理学家霍金在提出他的宇宙模型时,干脆给出了11维空间,认为要描述宇宙,X、Y、Z和T(时间)四个未知数是不够的,要加到11个未知数之后,才能够解释宇宙的很多结构。时间与空间非常复杂。它们是由混沌吐的两仪。天地万物,人间种种,皆自其中出。不谈它们之间可能衍生近乎无穷数的关系,仅以时间为例,若我们在一个更微观的量子层次去看,或许可以发现:时间始终在起伏摇晃,时缓时急,或轻或重,并不具备一个稳定不变的均质。其整个流动过程自始至终存在无数极为微小的空隙。这种流动过程在理论是可逆的。换而言之,这里的时间正在以一种陌生得令人惊讶的方式活动着,已完全不是我们日常经验里的时间。时间深处的那些空隙,是一处与时间无关的位置。我们或许能在那里逃离时间,不为其笼罩,开始观察,进而比较纯粹地叙述时间的维度及其可能性。也许,通过这种叙述,我们能认识到时间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它来于何处,要流向于何方?它决非是时钟所测量的两个点之间的量度。它更不是人的解释,而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仍然以《追忆似水年华》为样本,这种支离破碎的追忆过程,就不是过去文学评论讲的“记忆本身超出实际时间的流程之外”,而就是实际时间本身,是微观层面下的时间。我不是在说科幻。大家去读一下最前沿的物理学,读相对论、超弦理论、量子理论、黑洞物理等。物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和谐对称的原理,一个黄金分割比率,以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几何意义上的远近透视的对比。它们都是对神最伟大的赞颂。
量子物理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微观世界的基础。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的成就使得物理学从经典物理学发展到现代物理学。它们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基础。量子物理究竟提出了哪些革命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中又有什么样的用处?科学家们在研究原子、分子、原子核、基本粒子时所观察到的关于微观世界的系列特殊的物理现象与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隐秘、最微妙的部分又有着什么样的奇妙联系?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光既是波,又是粒子。通俗地讲,一匹马既是红色的,也是白色的。这可能吗?按照我们通常的想法,最有发言权的是牧人。牧人只会对提出这种愚蠢问题的人翻白眼。但,马,在微观层面的属性确实这样。任何物体,任何一种生命,都同时既有这种波粒两象性,只是因为质量太大,我们无法观测到它们的波动而已。现在的小说基本上已摆脱文革时期的高大全模式,一个人既是聪明的,又是愚蠢的;既是善良的,又是狠毒的。(绝大多数时候,善恶混为一体。杀人如麻的曾剃头也是同治中兴的曾圣人。)我们讲这是人性。人性为什么这样复杂?这其实是波粒二象性在作怪。而在文学批评上,比如《废都》,季羡林说,这是一部会流传下去的大作。另一些人说,这是一部格调低下的晦淫之作。大家的意见为什么分岐这般大?同样也是这样原因。光是粒子还是波,取决于观察方式。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同样是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方式。即阐释。作品其意义彰显的关键处是被叙述!被如何叙述!被谁叙述!去年,我说《兄弟》是垃圾,说它粗糙,结构畸形。现在反思,相对于它所书写的荒谬时代,它具有某种经典气质。一个文学作品是经典的,同时也是一部垃圾。这是传统文学话语体系所无法想像。但在量子文学的话语体系里却可以成为常识。相对于目前全球的严肃写作者来说,前者过于狭隘。
一九二七年,海森伯提出测不准原理。也就是当你观察到事物的时候,你已经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你的观察对象了。我们阅读某个文本,也就改变着这个文本。个体是有限的。有限是渡江之筏。无数个有限,可能就是无限。尽管我们永无法抵达无限——这种感觉类似宗教体验,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南美豹身上的毛纹。但我们能听到这头豹子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传出的吼声。阅读,都是误读,是一种扭曲的幻觉。我们所看见的并非就一定是叙述者曾抵达的某处。不妨说,包括叙述者本人都难以重新回到那个地方。苏珊?桑塔格写《反对阐释》,指出,“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阐释的工作实际上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者就是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所有已经完成的文本都是我们站在此岸向彼岸投出的火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高于现实世界的神话文本。是客观的、永恒的、超自然的。这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读者只能通过阐释,通过那白昼与黑夜、落日与玫瑰、更迭的四季、语言的宫殿来品咂这个“从诞生到死亡,从顶峰到深渊”的过程。测不准的原理始终贯穿于文学史。时代是观察的门。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种当下的观测方式。所以今天大红大紫的作家,明日无人问津。反之亦然。
测不准原理在文学创作中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比如,叙述越精细,就可能距离作者力图表现的“真实”越远。这是人们为什么推崇简约主义的根本道理所在。而不仅仅是因为简约有留白的韵。繁复不是不好,我个人就偏好繁复。关键是,繁复要有生气,不能是词与物的堆积,要是花瓣,每一根蕊都与蝴蝶发生关系,不能弄成五光十色的垃圾场。最好的物理学家是那些用试图用一道简明的数学公式表现最复杂的宇宙万象的人,最好的文学家就应该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关系着手衍生出无数复杂文本的人。混沌生太极,太极化两仪、两仪立三才,三才定四象,四象、五行、六弥、七宿、八卦、九宫,以及那个藏有水火之象由两条黑白鱼形构成的神秘之圆。又比如,大多人在写作过程中总爱做一个训诫者,迫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一种道德,而不是力图呈现那些不可言说的,把种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世界的真相由一系列的可能性组成。世界是黑的,也是白的;人是善的,也是恶的。这些黑白善恶有时可以清晰地被我们看见,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灰。再次,辩证法过去口口声声的“要系统的、全面的”看问题,其实就是扯淡。一切看法,都是偏见,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由于宇宙的无限性,任何人,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写作,必然是从个体出发。人的精神,在天地间,是一粒粒星辰。当这些星辰按宇宙的意志,以各自的亮度轮流出现在我们头顶的夜穹时,天空也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广度与深度。
再谈“薛定谔的猫”。猫的生死是打开盒子前的“客观存在”,又决定于打开盒子后的“观察”。这种观察不是发现,而是决定。正像哈姆雷特所说:“是死,还是活,这可真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盒子里这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猫?多宇宙理论认为猫并未叠加,而是“分裂”成了两只,一死一活,它们存在于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即:一个“意识” 一旦开始存在,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就必定永生!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量子退相干的理论。由于各种量子退相干的原因,“猫”这样的宏观物体不会稳定地处于一个相干叠加态上。“薛定谔的猫”告诉我们:在没有被观察之前,一切都处在不确定之中。一旦有了某一特定的结果,人们就只能认定它,并对此前任何的可能性都不予考虑。这个佯谬几乎要撼动人类固有的理性大厦。且不去讨论它在道德、法律等社会层面所可能引发的问题,就文学而言,它所具有的内涵是这样深刻。首先是文学创作。小说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包罗万象。它出现在作者脑海里,一旦形成文本,最后发表,其他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也意味着,最好的小说,应该是那些没写出来的小说。)作者叙事,塑造人物,无论句子看上去有多么凝炼、透明、准确,这些句子总是处于一种叠加状态,是一只暖昧不清的猫。所以,博尔赫斯说,“比喻更能接近事物之本质”。而这些句子也能引发起我们各自迥然相异的联想。看到玫瑰,有人想到老虎,有人想到河流,有人想到那一块浸透茶水的小甜饼。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